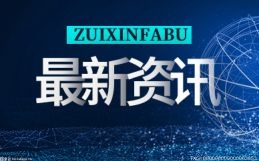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 关注 ”,方便您随时查阅一系列优质文章,同时便于进行讨论与分享,感谢您的支持~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拖延行为存在已久,追溯其历史发展,发现早在七百年前我国明代学者钱鹤的《明日歌》便是对我们日常生活中拖延现象进行描述,而国外则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学者开始对劳动者出现延迟、拖沓等一系列拖延行为进行研究。
拖延作为一种常见且复杂的现象,发生在不同年龄段的群体中,其中对国内外的大学生群体的学业拖延调查研究发现,国外大学生大约有80%-95%报告自己有拖延行为;而国内80%-90%大学生报告自己有拖延行为。
undefined
拖延行为对人们的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会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危害,对拖延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不同程度拖延行为对大学生造成学业、社交生活等问题。
其中高拖延者的学业成绩更差,同时表现出更低的生活幸福感,而进一步研究表明持续的拖延更是严重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尽管拖延是大众所熟知的概念,但几十年来都没能对拖延进行一个确切的定义,学者Steel等人综合了拖延的几个重要要素:回避、自愿和非理性,将拖延系统地定义为:尽管使人预见不利后果,但人们还是自愿推迟开始或完成计划的任务。
undefined
拖延的本质是个体的自我调控失败,研究发现自我控制功能分布在大脑的额区、额-中央区,Wu等人采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观察拖延行为与脑区的关系,发现拖延与大脑的腹内侧前额叶和腹外侧前额叶的静息功能连接呈现负相关关系。
即拖延行为越增加,额叶脑区的功能连接越减弱;学者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对拖延者的跨期决策研究,结果显示低拖延者在跨期决策选择任务时引发出顶枕外侧纹状区的N1成分和额区的P2成分,N1成分反映着个体注意力的加工过程。
P2成分则反映着个体注意资源的分配,高、低拖延者在N1、P2成分的差异表明了低拖延者在任务过程中能够投入更多的注意资源。
而高拖延者在任务加工和注意资源分配等自我控制功能受损。伴随着对拖延的自我控制理论的不断深入研究,拖延行为的发生被认为是由执行功能失败造成的。
执行功能最早由英国学者在研究额叶皮层损伤患者时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个体在完成复杂任务过程中,对思想、行为等各种基本认知过程进行协调和控制的高级的认知过程。
对执行功能的深入研究发现,执行功能并不只和前额叶皮层有关,对边缘系统等其他皮层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后来的学者不再将执行功能笼统地看作一系列统称的做法。
而是将执行功能定义为对某个认知方面的能力进行研究,通过前人的研究将执行功能分为三个相互联系又不同的子功能,即认知转换功能、记忆刷新功能以及抑制控制功能。
undefined
执行功能在认知过程中作为自我调节的重要部分,它会影响着个体的行为发生,研究发现拖延行为被划分为决策阶段和执行阶段,个体在任务时间决策阶段后,接下来便是进行任务的行为执行阶段。
而个体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由于认知功能失调导致其产生拖延行为,表明了执行功能和拖延行为有着重要联系,进一步研究发现拖延者的执行功能的核心子功能——抑制控制存在缺陷。
抑制控制作为执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在任务过程中阻止无关信息的干扰或者控制不恰当行为,以减少无关刺激对目标任务的影响。
研究发现抑制控制是个体执行任务过程中引起拖延的重要因素,Gustavson等人使用包括反扫视、Stroop和停止信号任务对拖延者的抑制控制进行研究,发现了拖延行为与抑制控制存在密切联系。
undefined
Rebetez等人也发现了在更复杂的任务过程中高拖延者表现出更差的抑制能力;国内学者张茹等人的研究同样发现大学生群体中不同程度拖延在执行功能上存在差异,高拖延得分者在执行功能比低拖延得分者表现更差。
吕丹萍与单瑞飞等人进一步研究发现,拖延与抑制控制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近几年来尽管对拖延与抑制控制的研究不断深入,但对拖延者的抑制控制的研究大部分还处于行为学层面上,而行为作为心理的一种外显反应。
其不能展示拖延者执行抑制控制功能时的认知神经特点,并且抑制控制在大脑作用过程中是快速的,需要对抑制控制的神经生理层面的观测才能了解拖延者抑制控制的认知加工特征。
undefined
因此,使用高时间率的事件相关电位技术探究拖延者的抑制控制的脑电生理特点。
研究发现情绪作为人们一种重要心理活动,在情绪情境下引起个体不同的情绪体验,会对个体认知和行为产生影响,如焦虑、内疚等负面情绪会加剧个体拖延行为。
因此,研究加入情绪变量进一步研究情绪对拖延行为的作用。情绪是指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和行为反应,由主观体验、外部表情和生理唤醒三要素组成,其不仅会影响个体的拖延行为的发生,也对执行功能甚至细化到认知抑制能力上也都存在影响。
研究发现抑郁和暴躁会影响个体的决策水平,从而导致执行抑制困难。研究表明拖延行为、情绪与抑制控制两两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但是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情绪对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呢?
undefined
针对这个问题,研究将情绪这种状态性因素加入拖延和认知抑制的研究中,进而全面地探究拖延行为的神经-心理机制。
高、低拖延者在情绪启动下认知抑制的行为学差异比较
在实验二中,高、低拖延者结合不同情绪的启动来进一步研究拖延、情绪与认知抑制控制三者之间的关系。
行为层面上,在Stroop范式任务中,高、低拖延者在正、负情绪的启动下反应时存在差异,具体表现在拖延者在正性情绪启动下完成任务的反应时短于负性情绪启动下的,表明拖延、情绪与认知抑制控制存在密切关系。
通过结果可以看出情绪影响拖延行为,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不同程度拖延者在正、负情绪启动下表现出抑制控制能力的差别,正性情绪使高拖延者增强认知抑制水平而负性情绪使其对认知抑制表现出削弱作用,导致其对反应冲突做出错误的判断。
这提示我们,正性情绪启动下更有可能提高拖延者的抑制控制能力,进而对注意资源的分配更加合理。
高、低拖延者在情绪启动下认知抑制的脑电生理差异比较
对拖延者脑电特征的结果分析,前期阶段N200的波幅表现出不同的差异,低拖延被试组在负性情绪启动下的N200波幅表现出显著激活,而高拖延没有被显著激活,这表明了高拖延者比较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
在正、负性情绪启动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在正性情绪启动下的注意资源分配正常,而在负性情绪启动下,注意资源分配失调、抑制控制能力受损程度较大,结果说明了情绪的调节可以使拖延学生抑制外界干扰信息,专心完成任务。
undefined
研究表明,N450成分主要与任务的冲突监控有关,研究的四个被试组在脑电的后期阶段的N450成分也存在差异,高拖延组在负性情绪启动下的N450的波幅和潜伏期显著高于其他三组。
这表明高拖延者受到负性情绪的影响,在任务冲突监控能力上存在不足,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在监控任务干扰信息上。
另外,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波幅下,N450成分不同刺激条件与电极点存在交互作用,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前额区电极点Fz的激活程度比额叶后区电极点FC1和FC2高。
这很有可能是因为额叶前区具有控制情绪的功能,并且在N450成分的潜伏期下高拖延者在不同情绪启动后,其不同刺激类型的表现不同,正性情绪拖延组的潜伏期显著短于负性情绪拖延组。
undefined
这说明了受不同情绪的影响下,拖延者在复杂的任务中会表现出不同的抑制监控能力,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情绪还与拖延者大脑额叶的前扣带回有关。
综上所述,研究通过神经生理层面证实了高、低拖延者在认知抑制控制的相关脑区在对应的神经系统活动中存在功能异常特征。
也证实了不同程度的拖延者在正、负情绪启动下,认知抑制相关的脑区也会产生不同的变化,反映了情绪影响拖延者的认知抑制。
结论
第一,大学生拖延行为与抑制控制关系密切,不同程度拖延者在认知抑制任务中表现出的功能激活减退反映其认知执行功能可能存在一定功能不足。
第二,情绪对不同程度的拖延者在认知抑制能力上存在差异,正性情绪能够促进高拖延者认知抑制的成功,负性情绪对其认知抑制能力具有削弱作用。
X 关闭
2022年中国家电行业一季度报告:国内累计销售额1540亿元
31省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97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1355例
南方强降雨再起 北方周末暖热回归
南方地区将有明显降水过程 黄海南部海域有大雾
吴谢宇弑母案二审因“不可抗拒原因”中止审理
X 关闭
240余万吨!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圆满完成民生供暖煤供应工作
厨电行业逆势增长 集成洗碗机是集成灶行业的下一个风口吗?
梦天家居2021年度净利润1.83亿元 同比增长7.04%
亚振家居发布2021年年度亏损公告 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1.53%
盾安环境9.71%股份转让悬而未决 一致行动人抛出减持计划